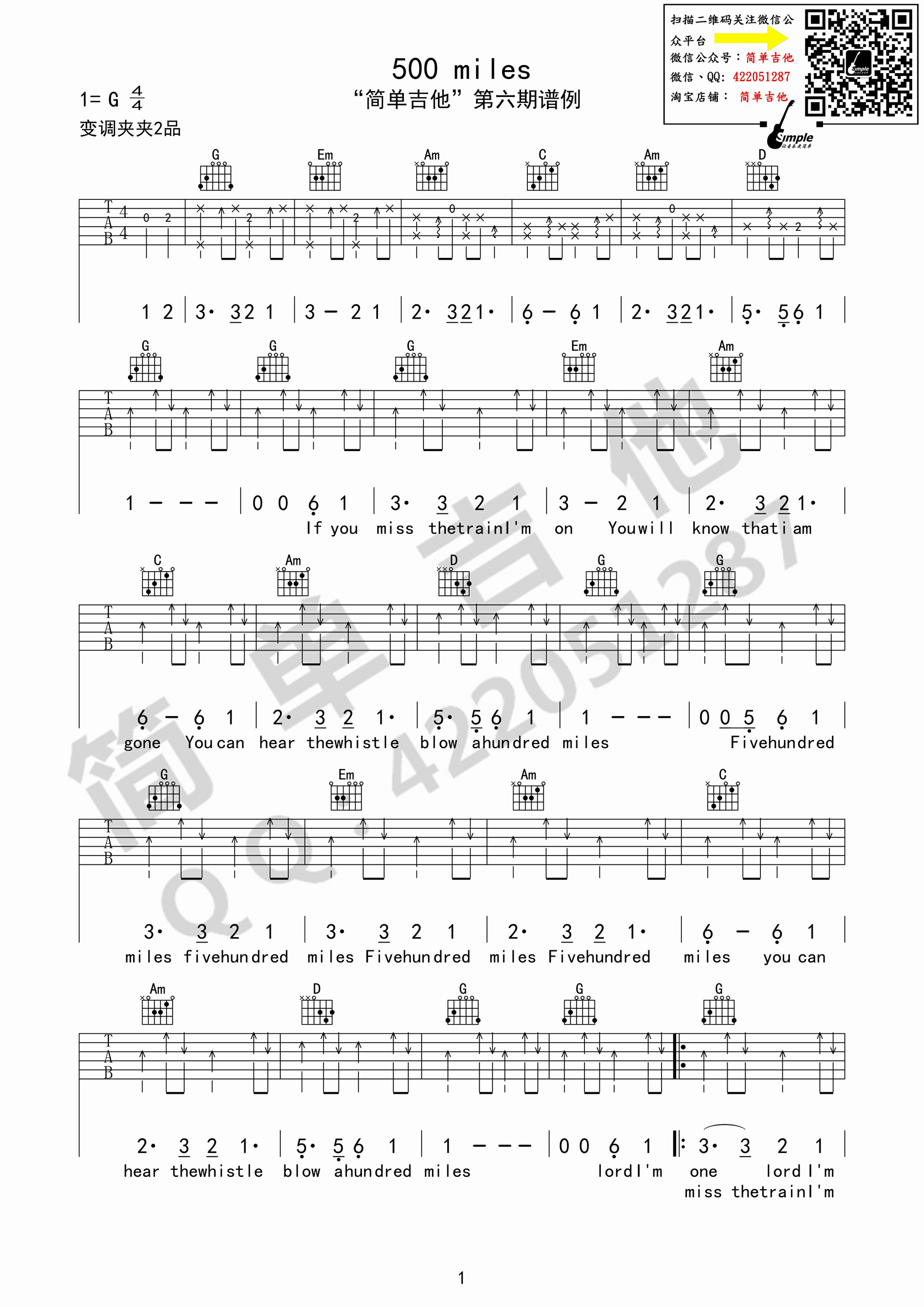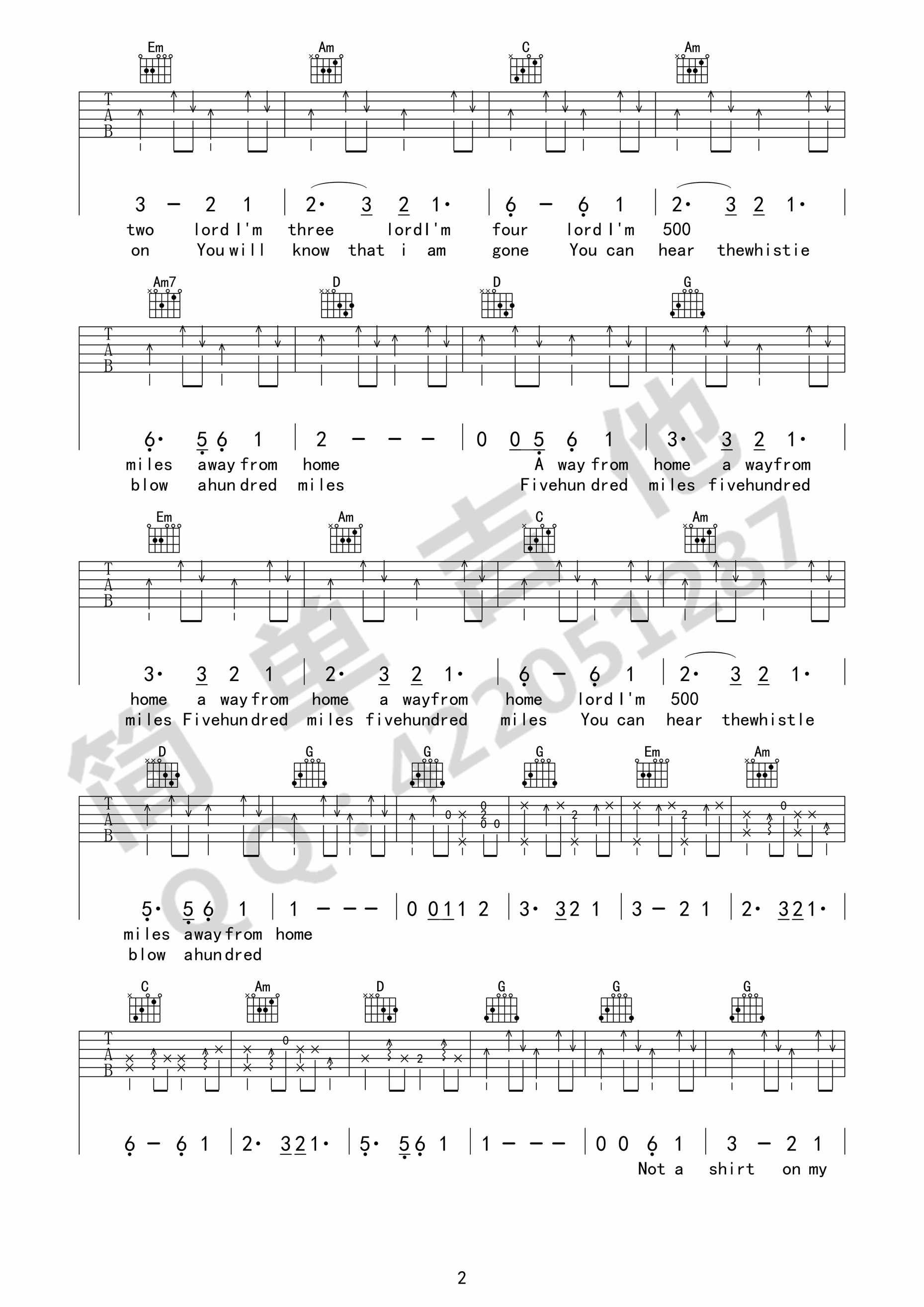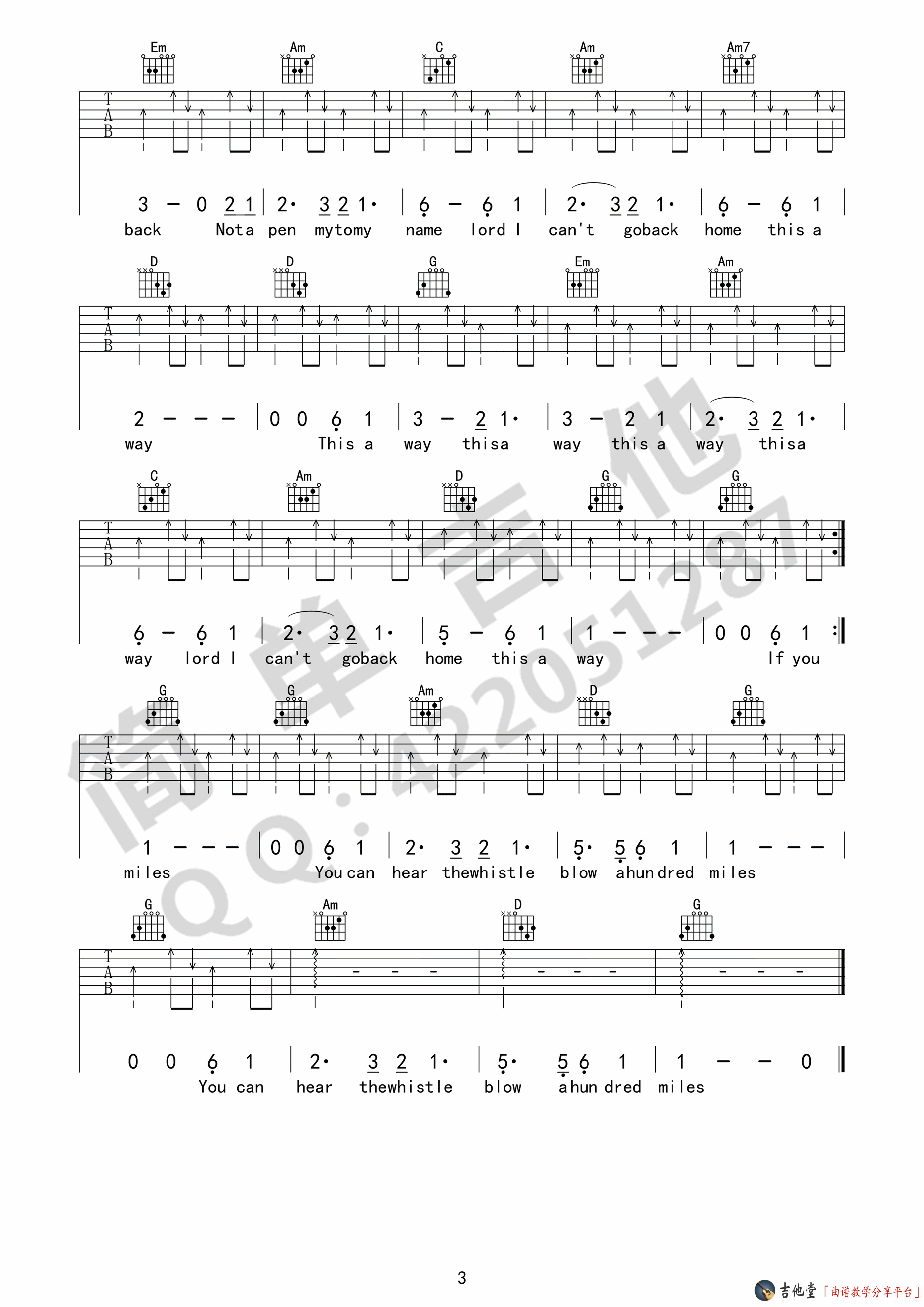《500英里》以质朴的歌词勾勒出漂泊者永恒的乡愁图谱。铁轨与里程的数字成为贯穿全篇的核心意象,五百英里的距离既是地理上的阻隔,也是心理上难以跨越的情感尺度。重复出现的"一百里、两百里"像列车轮毂般循环往复,在单调的节奏中堆叠出流浪者与故土渐行渐远的孤独轨迹。行李箱与旧衬衫的细节暴露出物质匮乏下的尊严困境,而汽笛声则化作命运无情的注脚,将主人公放逐在永动的迁徙循环中。歌词中暗藏的悖论令人玩味:离家的距离可以精确量化,但归途的可能性却始终处于悬置状态。这种数学般的精确与情感上的模糊形成微妙张力,使简单的民谣旋律承载起存在主义的重量。透过火车站台的氤氲蒸汽,可见现代文明进程中个体命运的缩影——当工业文明的铁轨无限延伸时,人类反而成了精神上的永久漂泊者。钞票与车票的反复权衡,揭示了经济理性对情感需求的碾压,而结尾处渐弱的和声则暗示着:在机械复制的时代里,乡愁终将成为不断稀释的记忆残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