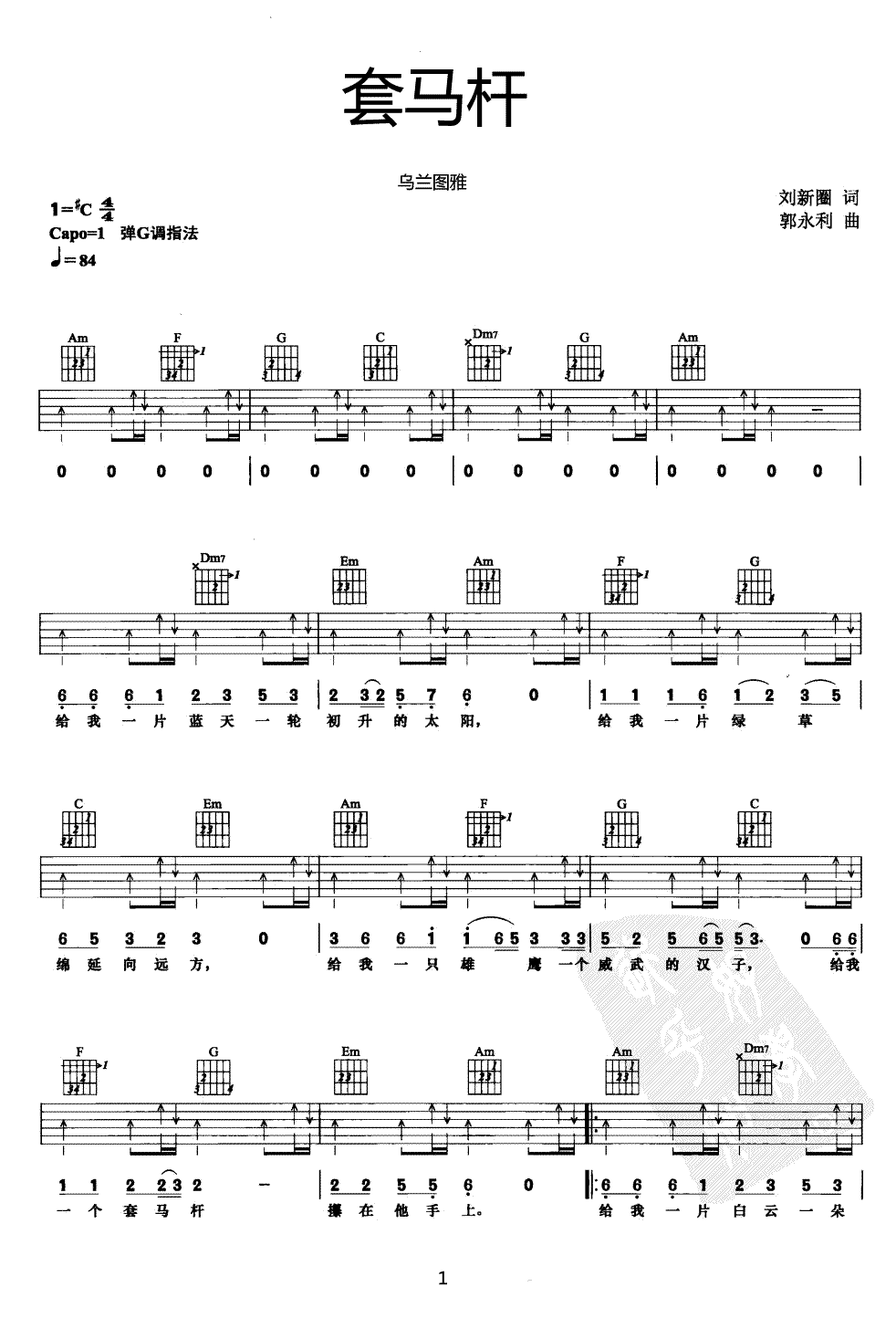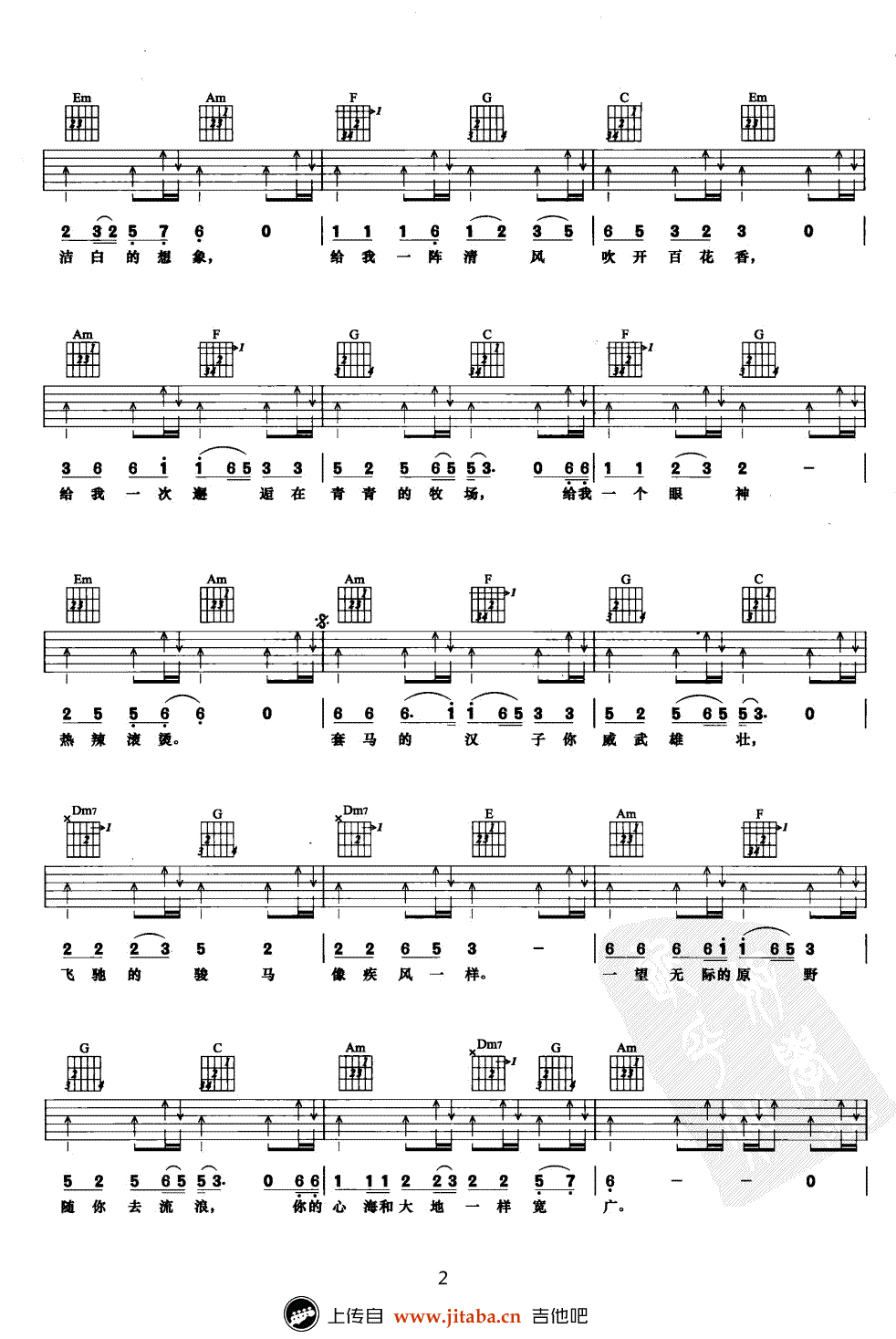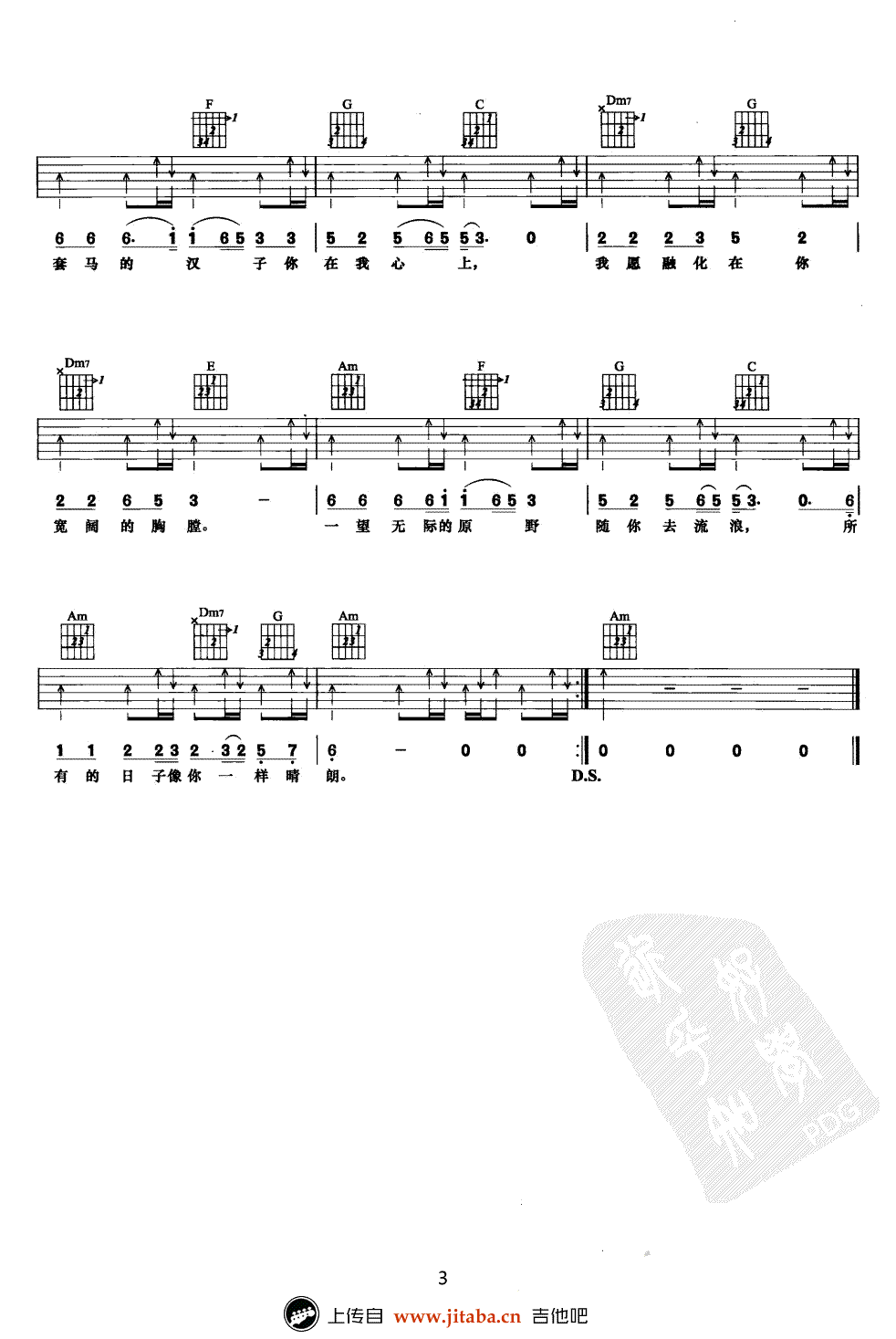《套马轩》以北方草原为背景,通过极具画面感的意象群构建出辽阔而苍凉的空间叙事。套马杆既是具体劳动工具,亦是精神象征——它代表着游牧文明中人与自然的角力与共生关系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“风撕扯云层”“草浪淹没马蹄”等意象,并非单纯写景,而是隐喻生命在严酷环境中的坚韧姿态。马群奔腾的节奏感与牧人呼麦声的交织,形成某种仪式般的原始张力,暗示着代际传承中未被现代文明稀释的野性灵魂。 歌词深处藏着对消逝传统的挽歌式凝视。“锈蚀的鞍钉”“褪色的鬃毛”等细节指向一种缓慢的消亡过程,但作者并未沉溺于感伤,转而以“勒进掌心的缰绳”“烧喉的烈酒”等痛感描写,凸显出蒙古民族在历史变迁中特有的沉默与骄傲。这种矛盾情感最终在“地平线吞没落日/篝火点燃星河”的宏大画面中得到升华——个体的渺小与自然的永恒形成辩证统一,传递出超越苦难的生命哲学:所谓永恒,恰在于无数短暂生命对自由的不灭追逐。 全篇通过物象与心象的叠加,完成对游牧文化的诗性重构。套马杆作为核心意象,既是穿刺天地线的武器,也是测量生命厚度的标尺,最终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图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