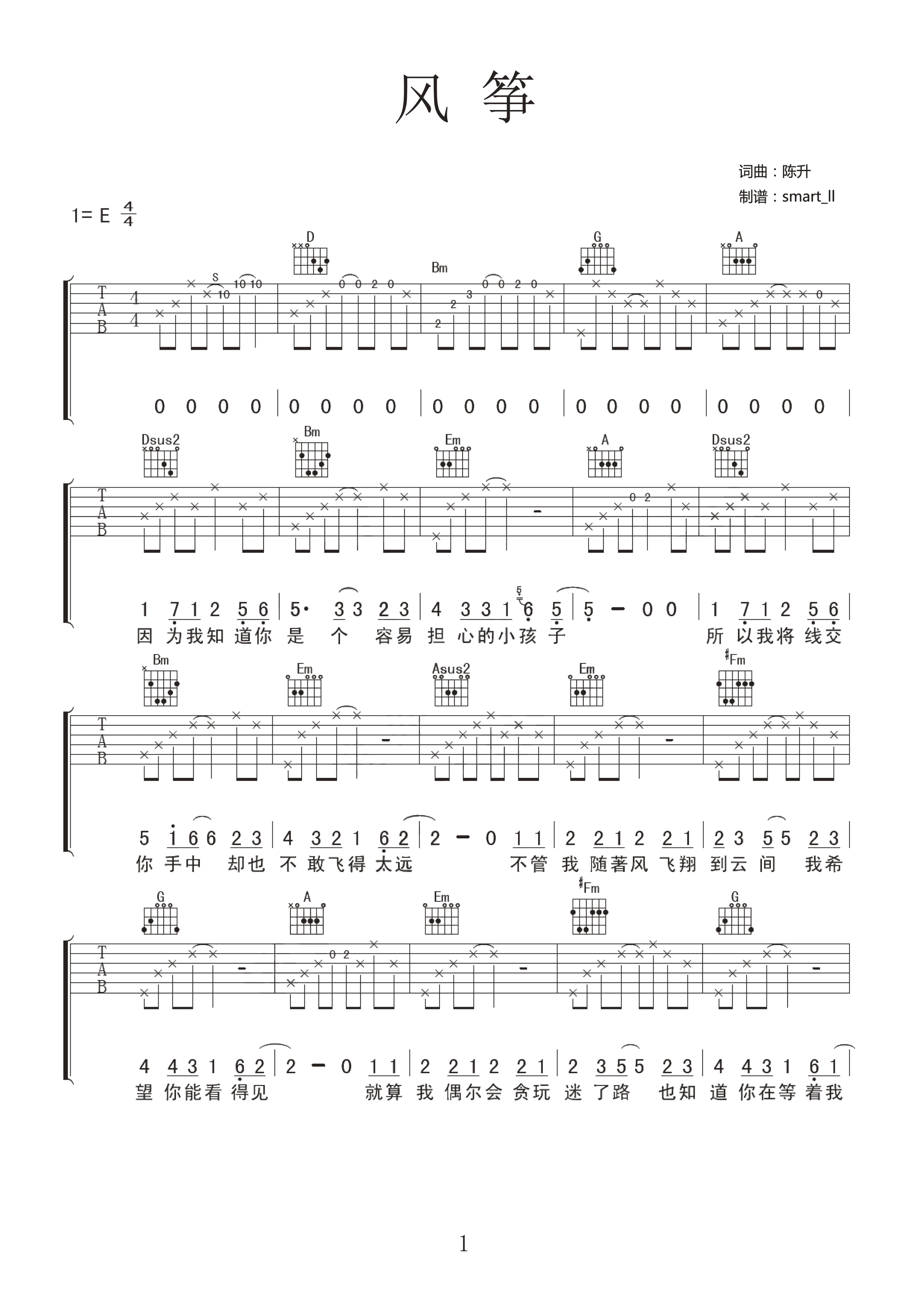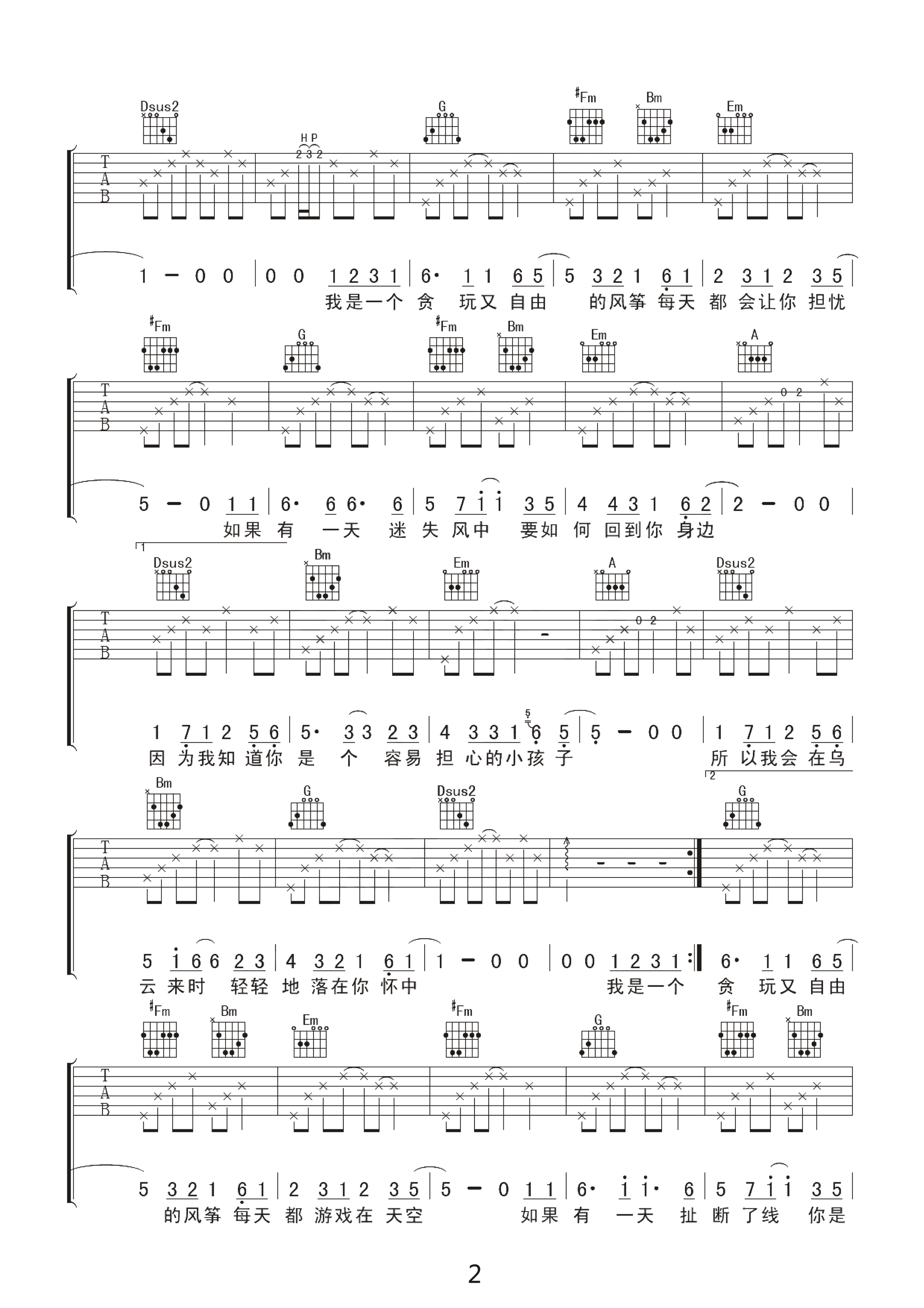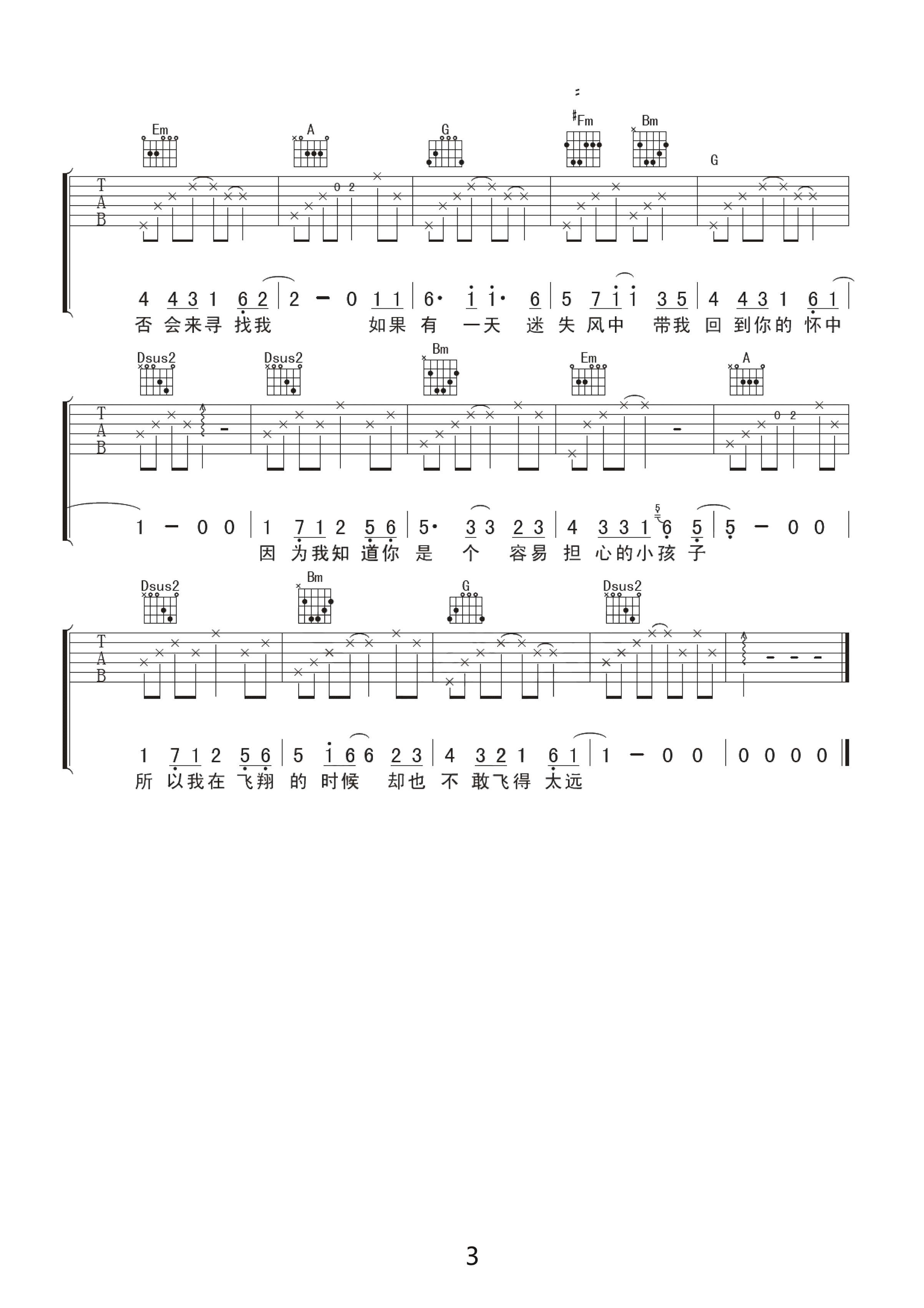《风筝》以意象化的笔触勾勒出生命在自由与牵绊间的永恒徘徊,通过风筝与线轴的二元关系隐喻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。歌词中飘摇的纸鸢既是理想主义的化身,又承载着现实重力的拉扯,那些"逆风时绷紧的弧线"恰似个体在时代气流中的挣扎轨迹。创作者将传统风筝工艺中的竹骨与绢纸转化为具有痛感的生命符号——看似轻盈的飞翔实则需要承受骨骼变形般的代价,这种矛盾性构成整首作品的张力核心。线轴意象被赋予双重象征:既是保护性的根系,又是禁锢性的锁链,当歌词反复质问"谁在收放之间丈量天空的宽容",实质上探讨的是人类永恒的生存悖论——对安全感的依赖如何消解对自由的渴望。季节变换的意象群暗示着命运的不可控性,春风与秋霜不再是自然现象,而成为机遇与挫折的诗意转喻。结尾处断线的留白处理颇具东方美学神韵,在失去束缚的瞬间,飘逝的风筝反而完成了对大地最深刻的回归,这种辩证思考使作品超越普通励志歌曲的层次,触及存在主义的哲学维度。全篇通过日常物象的陌生化处理,完成了一次对当代人精神漂泊的集体潜意识书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