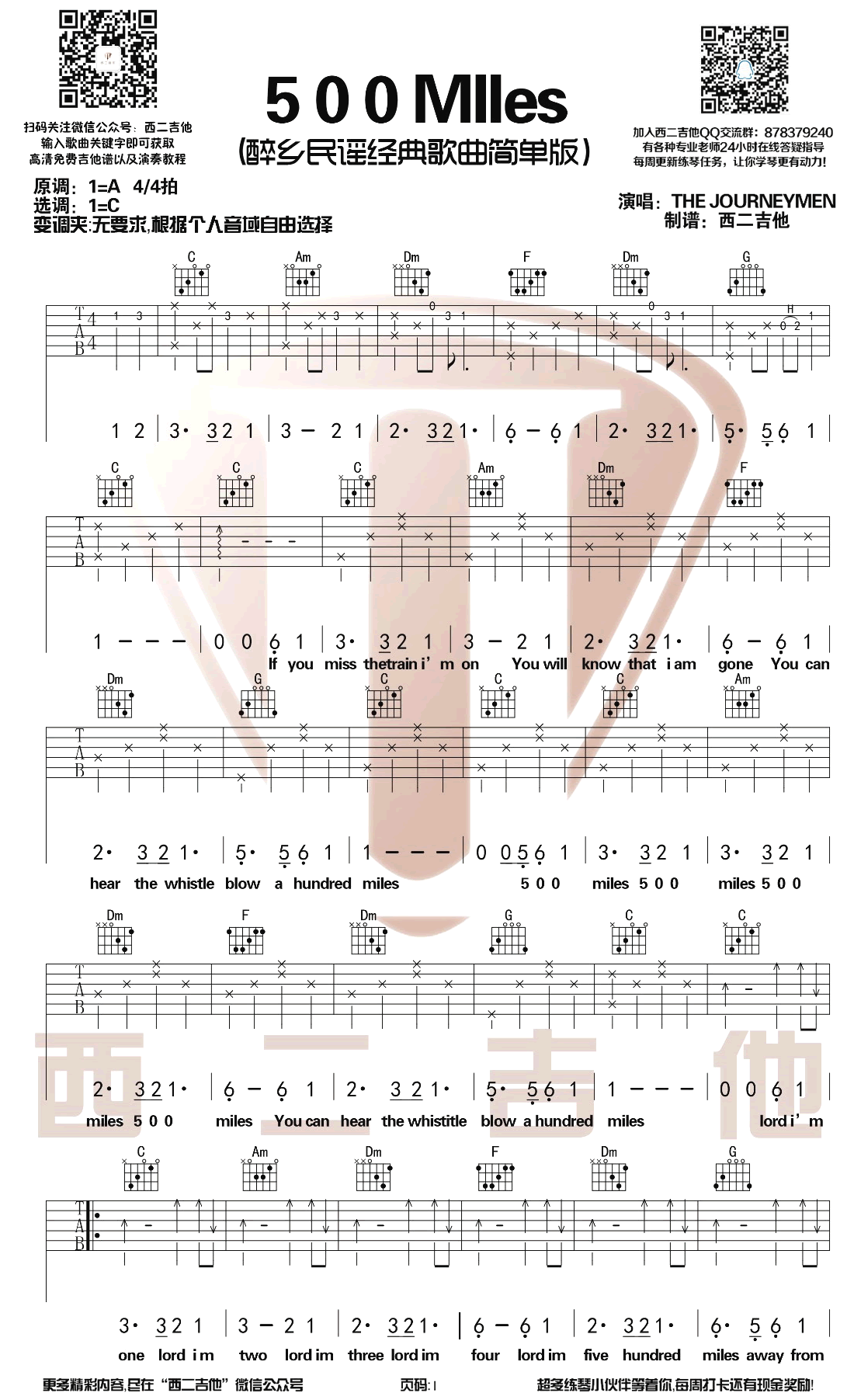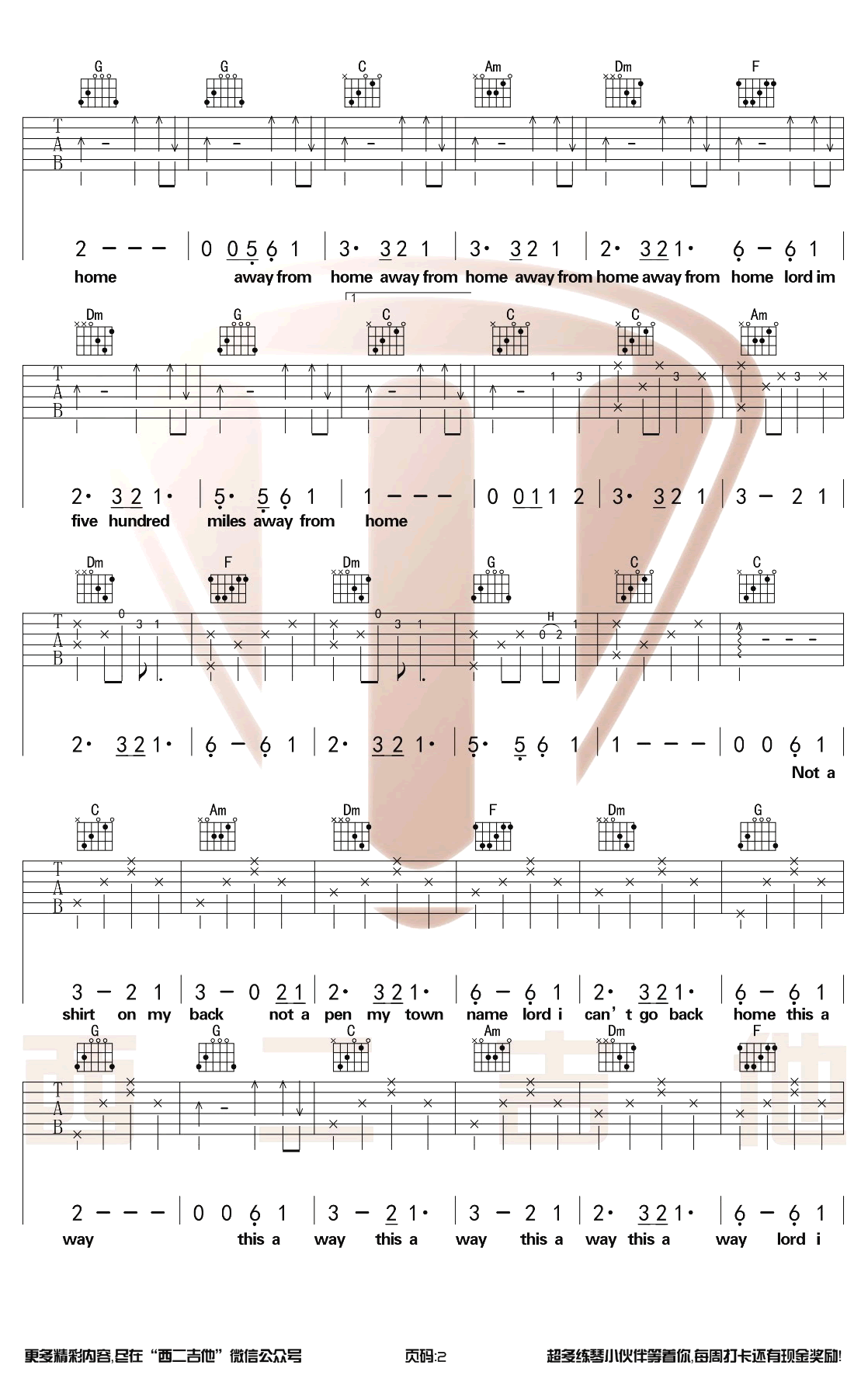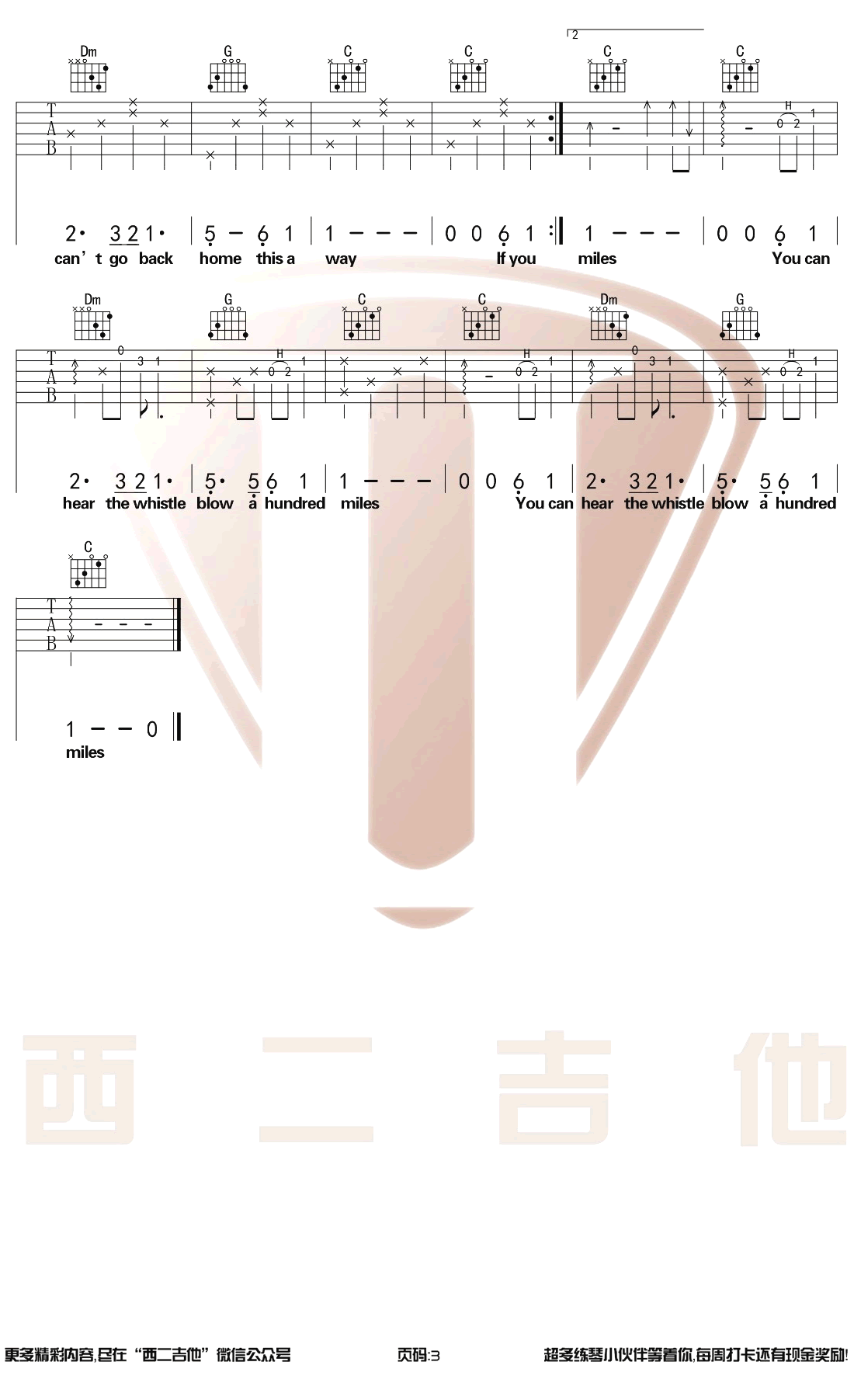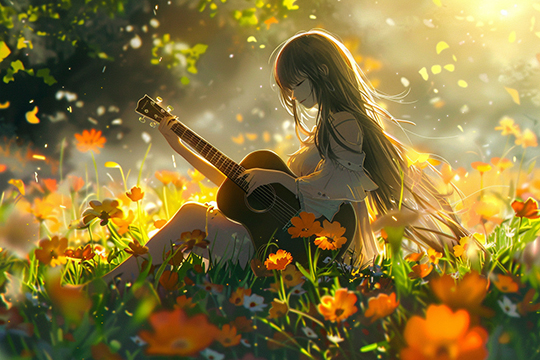《500 Miles》以简洁质朴的意象构筑了现代人永恒的漂泊困境。铁轨延伸的意象与重复出现的数字“五百英里”形成空间上的张力,物理距离在此转化为心理距离的隐喻。蒸汽时代工业文明的特有场景——火车、月台、汽笛声——被赋予深刻的象征意味,成为现代人精神流放的载体。歌词中未明确道别的离乡者,其沉默比任何痛哭更显孤独,衣袋空空的细节暗示着经济移民的无奈选择。不断叠加的距离数字形成递进式情感冲击,当里程从一百增至五百,归途的可能性随之递减,这种数学逻辑下隐藏着存在主义的荒诞。重复出现的“away from home”构成旋律般的执念,与火车节奏形成双重韵律,而始终缺席的“home”恰恰成为最强烈的在场。歌词通过交通工具的客观性反衬情感的不可测量,铁轨的线性时间否定了归期的循环可能,最终在汽笛声中完成对现代人无根性的白描。这种去抒情化的表达反而让漂泊感获得更普遍的共鸣,使作品超越具体时代成为人类迁徙宿命的永恒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