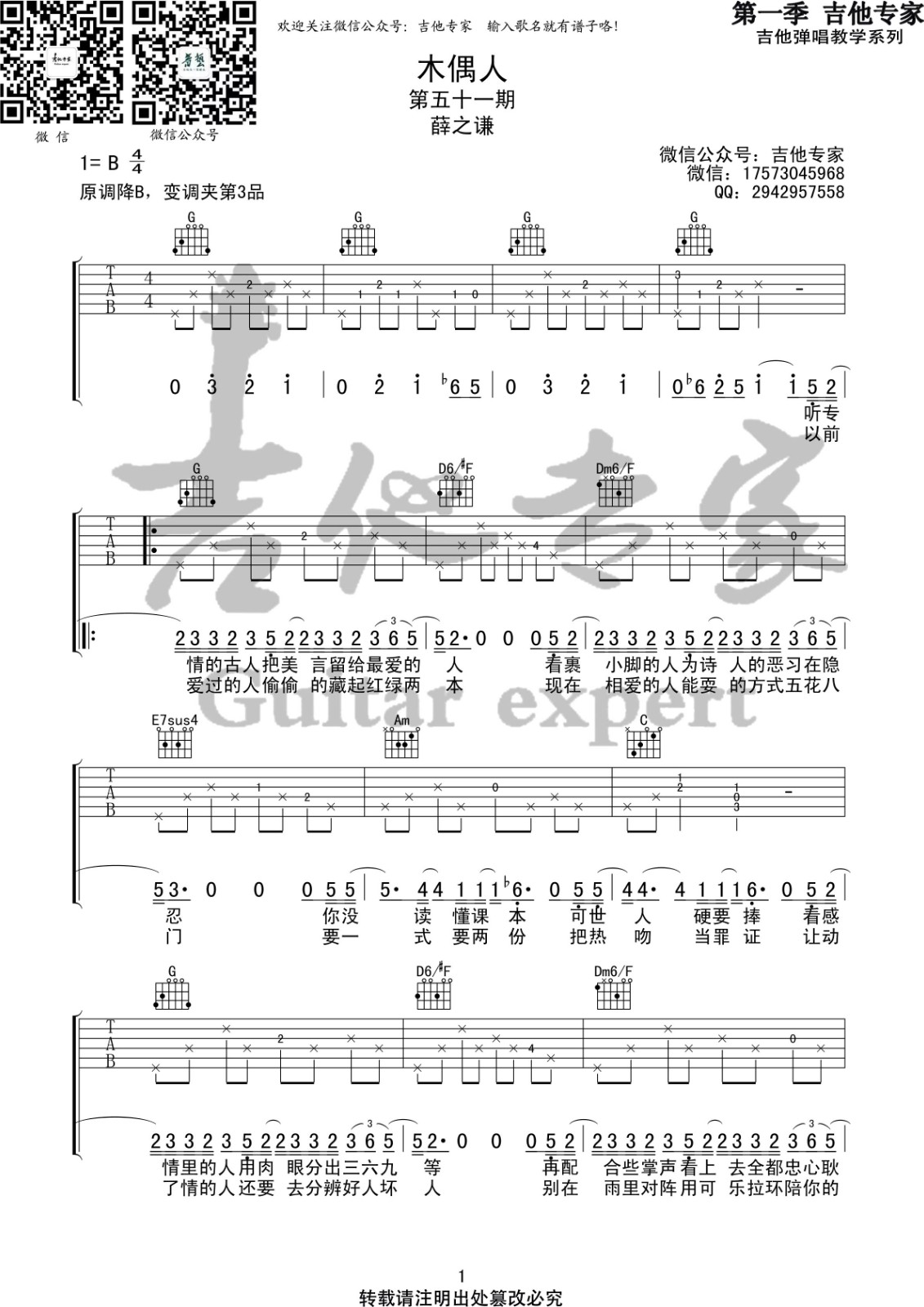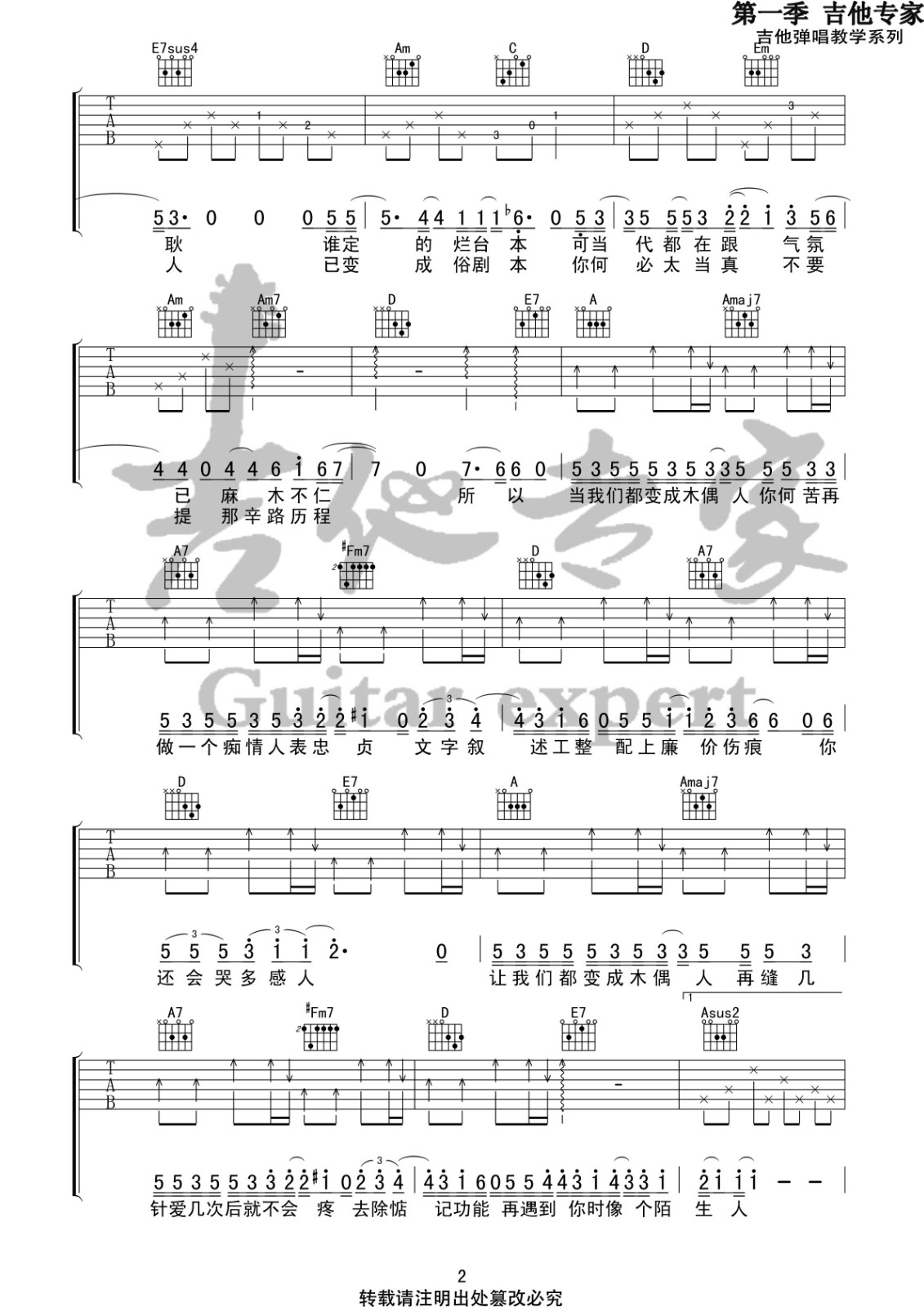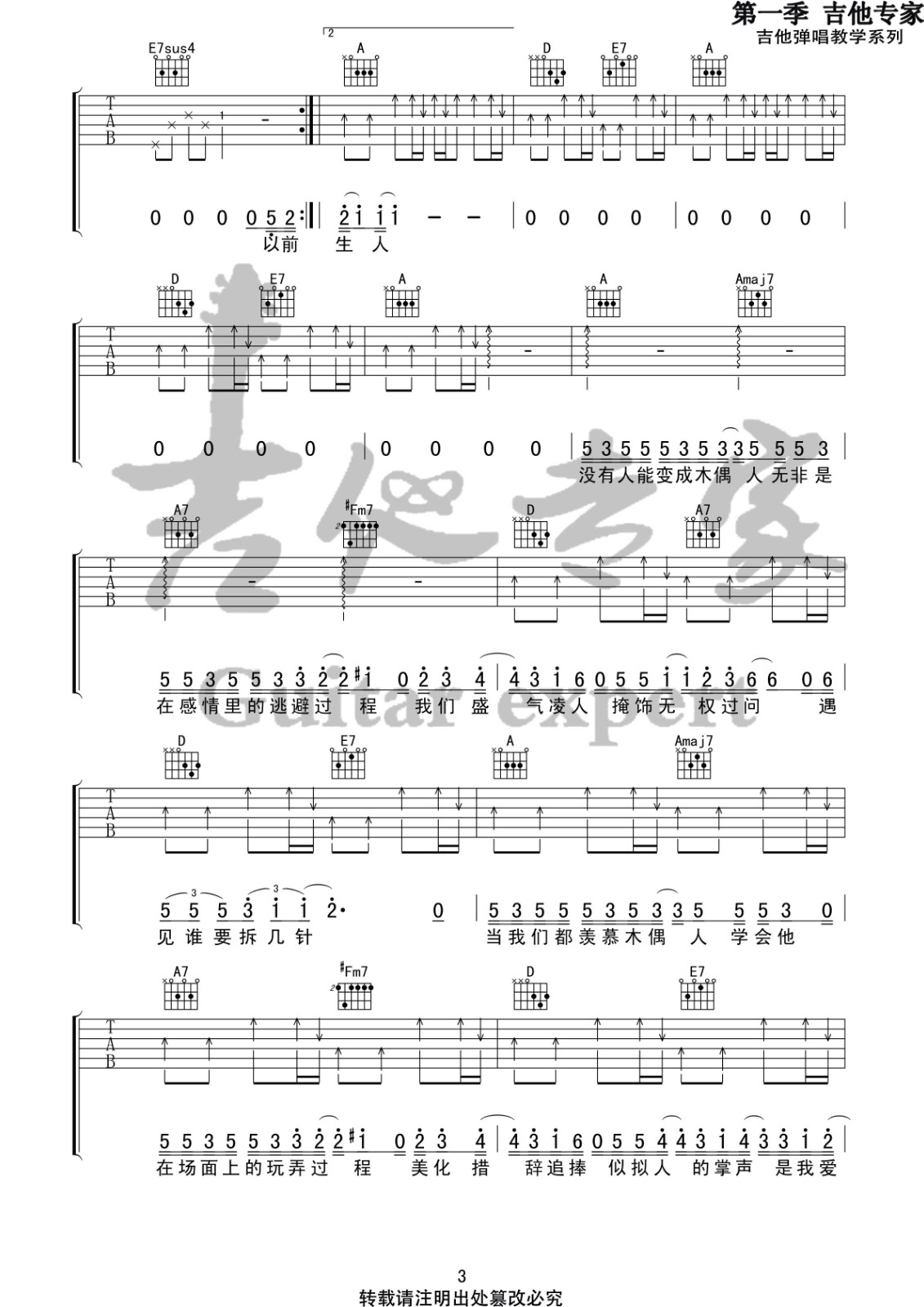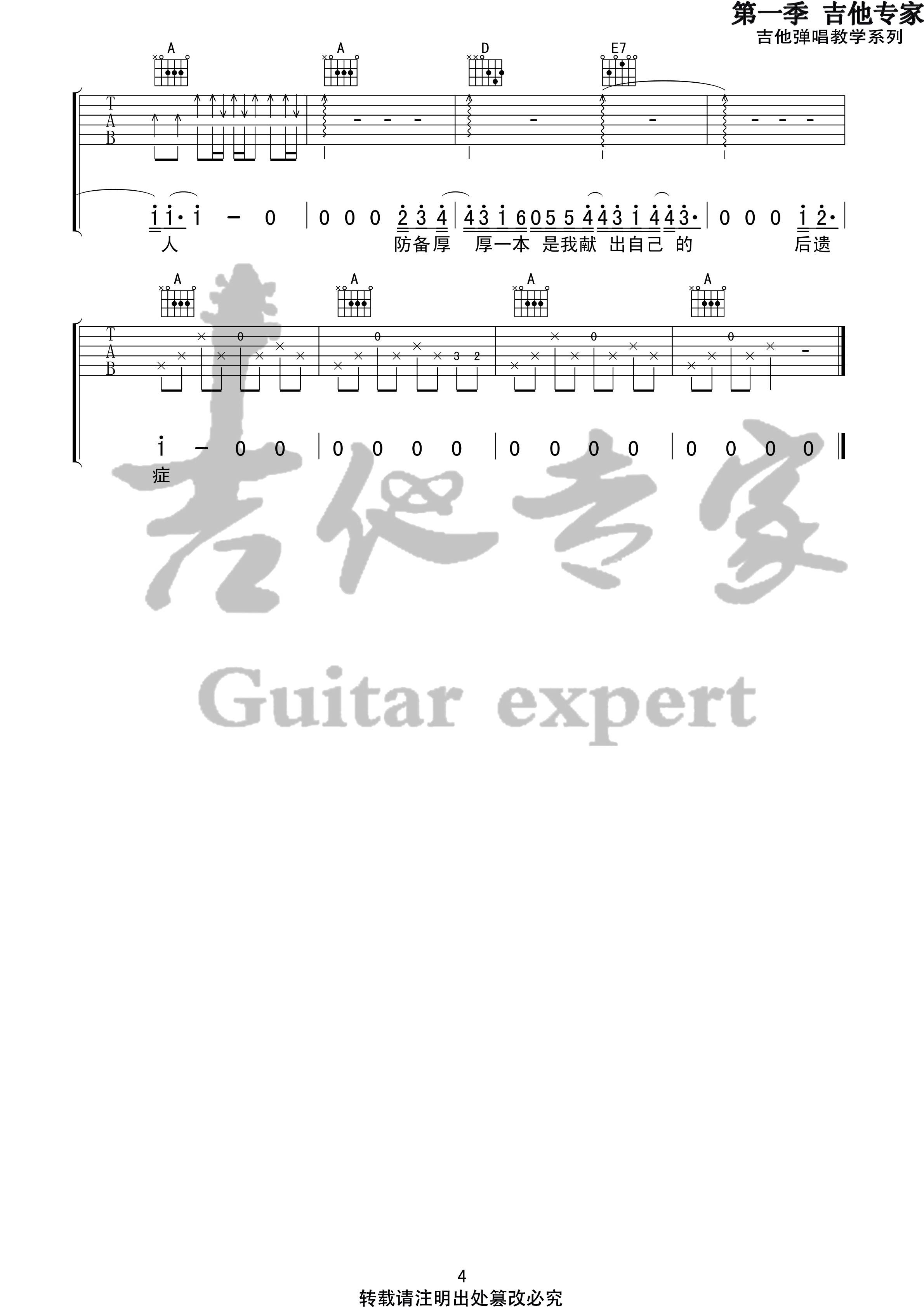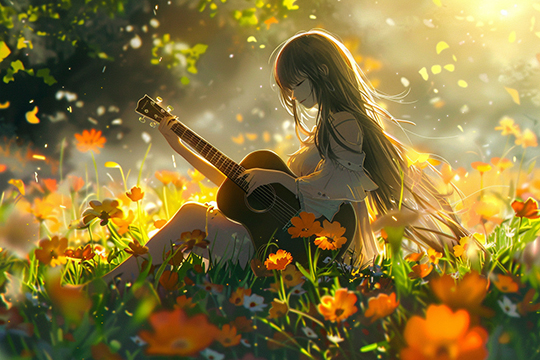《木偶人》以提线木偶为隐喻,探讨现代人精神困境与生存状态的深层命题。歌词中悬于半空的木偶形象,成为被无形力量操控的群体缩影,丝线既是社会规训的具象化呈现,也暗喻个体与命运之间的脆弱连接。机械重复的鞠躬动作构成对现代仪式化生活的尖锐讽喻,油彩覆盖的面具下藏着逐渐僵化的情感本能,这种内外分裂的状态揭示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时代的精神异化现象。副歌部分"掌声响起来我便活过来"的生存逻辑,直指他者认同对自我价值的粗暴置换,被观看者最终内化了观看者的期待,将外部评判体系转化为自我存在的唯一标准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笑与泪都由线牵引",暗示情感表达已成为程式化表演,当木偶开始习惯性模仿人类情绪时,人性反而在模仿中逐渐消解。创作者通过木偶视角的自我审视,呈现了当代人在社会角色与真实自我之间的永恒撕扯,那些被丝线勒出的红痕,既是体制规训的暴力印记,也是觉醒者痛感的最后证明。作品最终留下存在主义式的叩问:当所有动作都变成条件反射的表演,那个真正操纵命运的幕后主体是否也正在成为更大的木偶?